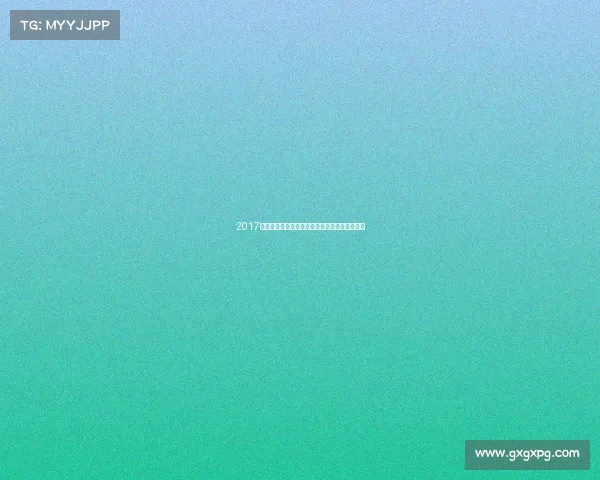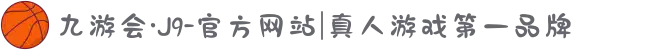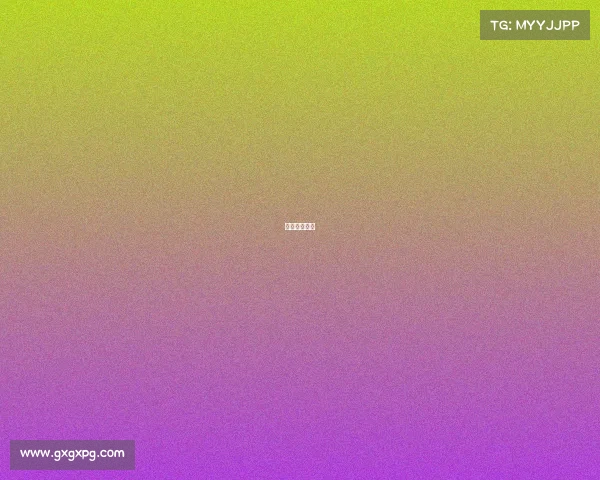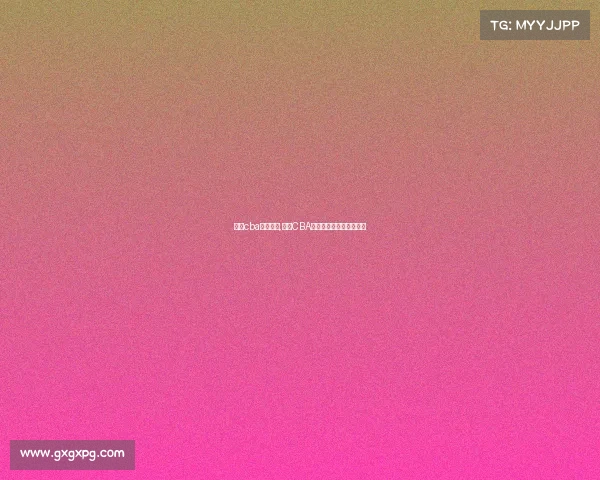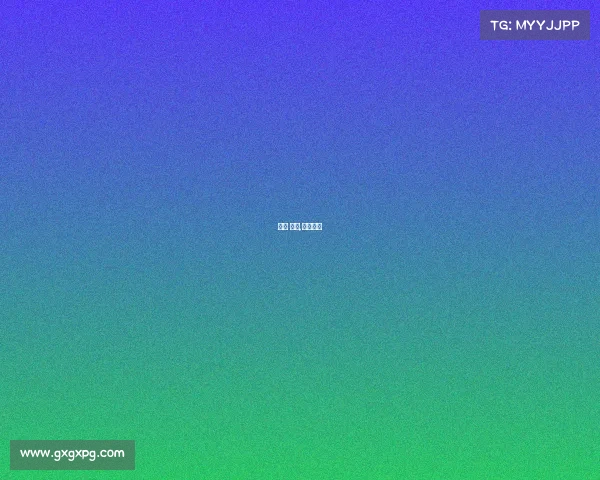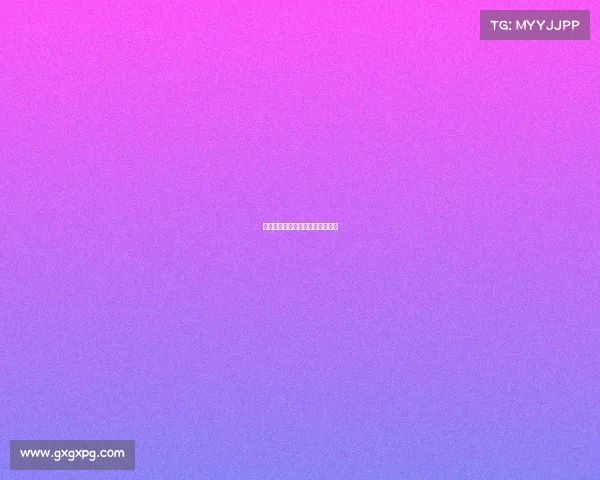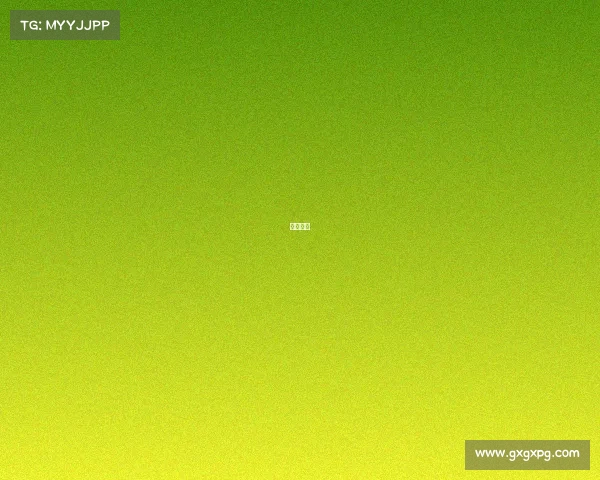1. зҺҜжө·еҚ—еІӣеӣҪйҷ…еӨ§еёҶиҲ№иөӣпјҲжө·еёҶиөӣпјү
ж—¶й—ҙпјҡ2017е№ҙ3жңҲ17ж—ҘвҖ“25ж—ҘпјҲе…ұ9еӨ©пјүдё»еҠһеҚ•дҪҚпјҡжө·еҚ—зңҒдәәж°‘ж”ҝеәңиөӣдәӢдә®зӮ№пјҡ第八еұҠиөӣдәӢпјҢдё»йўҳдёәвҖңж–°еҘҮдё–з•ҢВ·еҚҠеұұеҚҠеІӣжқҜвҖқпјҢ40ж”ҜиҲ№йҳҹеҸӮиөӣпјҢеҲӣдәҡжҙІзҰ»еІёиөӣ规模зәӘеҪ•гҖӮиҲӘзәҝжҖ»й•ҝ820жө·йҮҢпјҢеҲҶдёәIRCз»„пјҲе…ЁзҺҜ/еҚҠзҺҜпјүе’Ңз»ҹдёҖи®ҫи®Ўз»„пјҲд»…еңәең°иөӣпјүпјҢжҖ»еҘ–йҮ‘30дёҮе…ғгҖӮйҖ”з»Ҹдёүдәҡжө·еҸЈдёҮе®Ғйҷөж°ҙзӯүеёӮеҺҝпјҢи®ҫзҪ®иө·иҲӘд»ӘејҸеҸҠз»ҸеҒңжёҜйўҒеҘ–жҙ»еҠЁгҖӮ2. зҺҜжө·еҚ—еІӣеӣҪйҷ…е…¬и·ҜиҮӘиЎҢиҪҰиөӣпјҲзҺҜеІӣиөӣпјү
ж—¶й—ҙпјҡ2017е№ҙ10жңҲ28ж—ҘвҖ“11жңҲ5ж—ҘпјҲе…ұ9еӨ©пјүзӯүзә§пјҡжҙІйҷ…2.HCзә§пјҲдәҡжҙІйЎ¶зә§пјүиөӣдәӢдә®зӮ№пјҡ第еҚҒдәҢеұҠиөӣдәӢпјҢжҖ»йҮҢзЁӢ1566е…¬йҮҢпјҲеҺҶеұҠжңҖй•ҝпјүпјҢйҖ”з»Ҹе…ЁзңҒ17дёӘеёӮеҺҝпјҢи®ҫ9дёӘиөӣж®өгҖӮзҡҮеҗҺиөӣж®өпјҡ第дёғиөӣж®өвҖңдёүдәҡвҖ“дә”жҢҮеұұвҖқпјҢеҗ«2дёӘдёҖзә§зҲ¬еқЎзӮ№пјҢйҡҫеәҰеҲӣзәӘеҪ•гҖӮдёІиҒ”дёҮе®Ғзҹіжў…ж№ҫжҳҢжұҹжЈӢеӯҗж№ҫдә”жҢҮеұұж°ҙж»Ўд№Ўзӯүзү№иүІжҷҜзӮ№пјҢиһҚеҗҲжө·еҚ—иҮӘ然дёҺдәәж–ҮйЈҺе…үгҖӮ3. жө·еҚ—е„Ӣе·һеӣҪйҷ…马жӢүжқҫиөӣ
ж—¶й—ҙпјҡ2017е№ҙ12жңҲ24ж—Ҙдё»еҠһеҚ•дҪҚпјҡдёӯеӣҪз”°еҫ„еҚҸдјҡе„Ӣе·һеёӮдәәж°‘ж”ҝеәңиөӣдәӢдә®зӮ№пјҡжө·еҚ—зңҒе”ҜдёҖ银зүҢи®ӨиҜҒ马жӢүжқҫпјҢеҸӮиөӣдәәж•°15,000дәәпјҢи®ҫ全马еҚҠ马иҝ·дҪ 马项зӣ®гҖӮеӣҪеҶ…йҰ–еҲӣпјҡи®ҫзҪ®з»ҲзӮ№е…ій—Ёд»ӘејҸпјҢдёәжңҖеҗҺдёҖеҗҚйҖүжүӢйўҒеҸ‘еҘ–зүҢгҖӮж–°еўһеҚҠзЁӢжғ…дҫЈи·‘и·‘еӣўPKиөӣе№ҙйҫ„ж®өеҲҶз»„еҘ–зӯүеҲӣж–°и®ҫи®ЎгҖӮ4. жө·еҚ—еӣҪйҷ…ж—…жёёеІӣиҮӘиЎҢиҪҰиҒ”иөӣпјҲдә”жҢҮеұұз«ҷпјү
ж—¶й—ҙпјҡ2017е№ҙ9жңҲ23ж—Ҙең°зӮ№пјҡдә”жҢҮеұұеёӮеҶ…е®№пјҡеҢ…жӢ¬е…¬и·ҜеӨ§з»„иөӣиҚЈиӘүйӘ‘иЎҢпјҲдёүжңҲдёүе№ҝеңәиҮід»ҖжқҹпјүпјҢз”ұжө·еҚ—зңҒж–ҮдҪ“еҺ…дёҺдә”жҢҮеұұеёӮж”ҝеәңдё»еҠһгҖӮиҒ”еҠЁе…ЁзңҒиҮӘиЎҢиҪҰеҚҸдјҡеҸҠдҝұд№җйғЁпјҢжҺЁеҠЁзҫӨдј—дҪ“иӮІеҸ‘еұ•гҖӮжҖ»з»“дёҺзү№зӮ№
| иөӣдәӢеҗҚз§° | ж—¶й—ҙ | 规模/йҮҢзЁӢ | ж ёеҝғдә®зӮ№ |
|--|-||-|
д№қжёёдјҡj9е®ҳж–№зҪ‘з«ҷзңҹдәәжёёжҲҸ| зҺҜжө·еҚ—еІӣеӨ§еёҶиҲ№иөӣ | 3жңҲ17ж—ҘвҖ“25ж—Ҙ | 40ж”ҜиҲ№йҳҹпјҢ820жө·йҮҢ | дәҡжҙІзҰ»еІёиөӣ规模зәӘеҪ• |
![2017е№ҙжө·еҚ—иөӣдәӢиҫүз…Ңзӣӣе®ҙзӮ№зҮғе…Ёж°‘жҝҖжғ…е…ұдә«з«һжҠҖиҚЈиҖҖ 2017е№ҙжө·еҚ—иөӣдәӢиҫүз…Ңзӣӣе®ҙзӮ№зҮғе…Ёж°‘жҝҖжғ…е…ұдә«з«һжҠҖиҚЈиҖҖ]()
| зҺҜжө·еҚ—еІӣиҮӘиЎҢиҪҰиөӣ | 10жңҲ28ж—ҘвҖ“11жңҲ5ж—Ҙ | 1566е…¬йҮҢпјҢ9иөӣж®ө | вҖңзҡҮеҗҺиөӣж®өвҖқйҡҫеәҰеҚҮзә§ |
| е„Ӣе·һеӣҪйҷ…马жӢүжқҫ | 12жңҲ24ж—Ҙ | 15,000дәәеҸӮиөӣ | йҰ–еҲӣе…ій—Ёд»ӘејҸ |
| иҮӘиЎҢиҪҰиҒ”иөӣпјҲдә”жҢҮеұұпјү| 9жңҲ23ж—Ҙ | еӨҡдҝұд№җйғЁиҒ”еҠЁ | иһҚеҗҲе…Ёж°‘еҒҘиә« |
2017е№ҙжө·еҚ—иөӣдәӢд»ҘвҖңеӣҪйҷ…еҢ–+е…Ёеҹҹж—…жёёвҖқдёәж ёеҝғпјҢиҰҶзӣ–еёҶиҲ№иҮӘиЎҢиҪҰ马жӢүжқҫдёүеӨ§йўҶеҹҹпјҢж—ўеұ•зҺ°жө·еҚ—иҮӘ然з”ҹжҖҒдјҳеҠҝпјҲеҰӮзҺҜеІӣжө·еІёзәҝзғӯеёҰйӣЁжһ—иөӣйҒ“пјүпјҢд№ҹйҖҡиҝҮеҲӣж–°и®ҫи®ЎпјҲеҰӮе„Ӣ马关门д»ӘејҸпјүжҸҗеҚҮиөӣдәӢдәәж–Үд»·еҖјпјҢжҺЁеҠЁдҪ“иӮІдёҺж—…жёёж·ұеәҰиһҚеҗҲгҖӮ